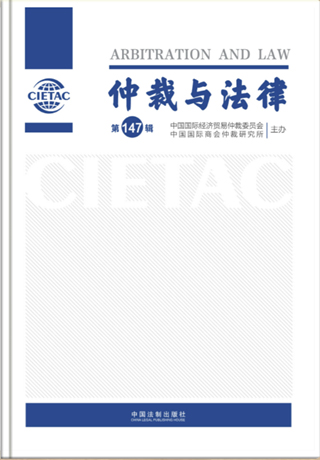
朱子琳*
摘要: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是指反垄断争议能否以仲裁方式解决,其中较有争议的是平等市场经营者之间因限制竞争行为产生的反垄断争议是否具备可仲裁性。基于反垄断争议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仲裁并不适宜解决此类纠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先后认定反垄断争议不可仲裁,其理由可归纳为三点:现行法规定存在空白、反垄断法具有公共政策性、反垄断争议涉及公共利益突破双方约定。然而细加审视可以发现,上述理由均有待商榷:其一,现行法并未否定仲裁解决反垄断争议的可能性;其二,公共政策本身内涵模糊,应当严格限制适用;其三,仲裁庭对反垄断争议的认定仅限于争议双方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影响其他利益相关方通过其它方式维护权利。从应然路径上看,当事人约定的仲裁条款在反垄断争议中应为有效,仲裁庭可在约定范围内解决其纠纷,法院可在仲裁裁决作出后审查该裁决是否有违反公共利益或公共政策的情形,而没有必要在事前一概否定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总体而言,中国司法机关应以更务实和开放的态度,认可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
关键词:反垄断争议 可仲裁性 公共政策 意思自治 司法审查
引言
反垄断争议,包括主管机关与实施垄断行为的经营者之间产生的行政争议,和市场经营者之间因限制竞争行为而产生的民事赔偿争议。 1 对于前者,因主管机关处于行政管理地位,与经营者之间并非平等法律关系,其争议因缺乏仲裁合意而无可仲裁的空间,本文不做过多讨论;对于后者,因作为平等市场主体的经营者之间可能存在仲裁合意,其争议能否提交仲裁则存在分歧,本文主要对此展开论述。下文如无特别指出,“反垄断争议”均指经营者之间的争议。
传统上,经营者之间的反垄断争议被视为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而用于解决私人之间商事纠纷的商事仲裁,则因为其私法性质而被认为与反垄断争议解决无涉。 2 随着实践与理论的演进,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国家和组织逐渐放弃了反垄断争议严格排除仲裁的观点。与之相对,中国法院在实践中对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仍持否定态度:尽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在2019年6月的一起案件中根据合同解释原则认为该案反垄断争议落入双方仲裁条款中,肯定了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 3 但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 4 和最高人民法院 5 (以下简称最高法院)先后在2016年和2019年8月基于中国法无明确规定、反垄断法的公共政策性以及反垄断纠纷涉及公共利益而否定了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然而,法院对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的保守态度仍遭到质疑:其一,在中国法语境下,采用仲裁解决反垄断争议是否有其适用空间?其二,公共政策是否足以排除通过仲裁解决反垄断纠纷?其三,应如何理解反垄断法涉及的公共利益?此外,若涉及反垄断的争议一概被归入不得仲裁之列,合同双方之间达成的仲裁协议便无法发挥作用,这是否会影响商事主体交易的可预期性?
上述问题表明,仅仅基于公共利益而一概否定反垄断纠纷的可仲裁性,或许并不是合理的选择。如何理解并化解反垄断争议与仲裁之间的冲突关系,是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从中国法院的三起裁定结果出发,结合实践演进与理论研究,探讨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除了引言和结语,文章主要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传统视角下反垄断争议与可仲裁性之间的矛盾,为本文的讨论奠定基础;第二部分回顾中国法院在三起案件中对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的裁定,分析由此产生的问题;第三部分探讨在中国法语境下,以仲裁方式解决反垄断争议的可行性;第四部分讨论公共政策对反垄断争议解决方式的影响;第五部分讨论公共利益对仲裁解决反垄断争议的影响;第六部分讨论仲裁解决反垄断纠纷的过程中,司法介入的应然路径。
一、传统观点:反垄断争议不具备可仲裁性
反垄断法肇始于19世纪末美国的《谢尔曼法》,自诞生时就带有自由企业的大宪章之称号,旨在维护市场公平、自由的竞争秩序。垄断行为是指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滥用或者谋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而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由于垄断行为不仅会损害其他竞争者的利益,还会影响市场秩序,并进而损害消费者福利,因而反垄断并不仅仅是维护其他竞争者利益,更重要的是恢复被破坏了的市场秩序、维护正常竞争状态。由此,反垄断法被认为是超越了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公法性质。 6
与之相对,仲裁的基础则在于当事人意思自治。仲裁庭管辖权的基础有二,其一是当事人的仲裁协议,其二是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所谓可仲裁性,即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某项争议能否通过仲裁解决;如果纠纷不具有可仲裁性,当事人即便约定了仲裁,仲裁庭也无法行使管辖权,仲裁庭对不具备可仲裁性的事项作出裁决的,仲裁裁决将遭到法院的撤销,或不被承认和执行。 7 《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即规定,若“依该国法律,争议事项系不能以仲裁解决者”则法院可以拒绝执行仲裁裁决。因此,可仲裁性是判断特定争议是否可以通过仲裁解决的重要标准。可仲裁性的标准包括可处分性、可诉讼性、商事争议、经济利益等。 8 从反面来看,如果争议涉及到公共利益,就超越了当事人之间可以自由处分或和解的范围,不能通过仲裁解决。
反垄断争议不具备可仲裁性,正表现在反垄断所代表的公共政策与仲裁所维护的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反垄断法意在恢复市场正常的竞争秩序,而不仅限于维护某个企业的私人权益;企业因垄断行为受到的侵害,涉及的也不仅仅是企业本身,还有相关市场的竞争状态和下游的消费者福利。因而传统的观点是,反垄断争议涉及一国公共利益,超越了私人利益的范围,无法完全由当事人自行处分,也不适宜由仲裁庭裁决,不具有可仲裁性。
反垄断争议不可被仲裁的原则,最早在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判决的1968年的“美国安全设备公司诉马奎尔公司案”(以下简称美国安全案)中得到确立。 9 在该案中,被告希科克制造公司(Hickok Manufacturing Co., Inc.,以下简称希科克公司)是一家生产男士背带服装等物品的制造商,原告美国安全设备公司(American Safety Equipment Corp.,以下简称美国安全公司)是希科克公司的商标被许可人,双方订立了15年的商标使用合同,并约定了仲裁条款。在该案中,美国安全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认定许可协议因违反《谢尔曼法》自始无效,因为其加剧了希科克公司的商标垄断。由于双方约定了仲裁条款,受理该案的法院裁定中止诉讼,提交仲裁。美国安全公司对法院的管辖权裁定提出上诉,上诉法院最终裁定反垄断争议不具有可仲裁性,支持了美国安全公司的上诉请求。上诉法院认为,首先,保护公共利益的反垄断法与保护私人利益的仲裁之间存在冲突,采用私人手段解决反垄断争议无法实现《谢尔曼法》下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目的。其次,商事仲裁员来自于商界,容易受商业利益影响,不适宜裁决具有公法性质的反垄断争议。再次,反垄断争议往往较为复杂,法院更具有相应专业能力。最后,若当事人一方具有垄断地位,他们之间的仲裁协议也很可能并非真实意思表示。因此,反垄断争议不应由仲裁解决。 10
总的来看,传统观点认为,经营者之间的反垄断争议不仅涉及到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也会涉及到相关市场中其他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仲裁仅关涉合同双方对争议处理的约定,故反垄断争议难以落入仲裁的范围内。
二、中国法院对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的实践分歧与问题
实践中,中国法院对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存在分歧。更多时候,法院认为反垄断争议不具备可仲裁性,但也有法院在部分案件中认可了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例如,江苏高院和最高法院就先后在两起案件中认定反垄断争议不可仲裁。不过,北京高院则在另一起案件中作出了相反认定。在下文将首先介绍这三起案件,随后分析由此产生的问题。
(一)江苏高院与最高法院:否定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
在江苏高院2016年裁定的“南京嵩旭公司诉三星中国公司案”(以下简称嵩旭公司案)中,江苏高院以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为由否定了反垄断纠纷的可仲裁性。该案中,原告嵩旭公司向南京中院起诉三星公司,控诉三星公司以不合理高价销售产品和强制搭售等垄断行为,而三星公司则以双方已经约定仲裁条款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在二审中,江苏高院认为,垄断民事纠纷不可以由仲裁解决,理由主要有三:第一,反垄断法的执行主要依靠行政机关,对垄断纠纷民事诉讼的管辖则仅限定在特定范围的法院。第二,反垄断法具有明显公法性质,且中国反垄断法实施时间短,尚未形成成熟的执法司法经验,尚未有对反垄断纠纷进行仲裁的实践。第三,反垄断纠纷不仅关涉当事人双方,还可能影响到其他经销商、所有三星公司产品的消费者的利益,该类纠纷已经突破了合同双方之间的仲裁约定。 11 因而,江苏高院最终驳回了三星公司的管辖权异议。
上述裁判决定和理由在最高法院2019年裁定的“壳牌(中国)公司与汇力公司横向垄断协议纠纷案”(以下简称汇力公司案)中也有所体现。该案中,原告汇力公司向法院起诉壳牌公司的行为构成横向垄断协议。在上诉中,壳牌公司以双方存在仲裁条款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最高法院在二审中否定了反垄断纠纷的可仲裁性,其理由与江苏高院的说理十分相似:第一,现行法下垄断行为的认定和处理主要依靠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民事诉讼,并未明确包括仲裁;第二,仲裁法解决的争议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而该案中双方之间的争议是垄断民事纠纷,而非合同纠纷;第三,反垄断法具有明显公法性质,是否构成垄断的认定超出合同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12 基于上述原因,最高法院再次否定了仲裁条款可以适用于反垄断纠纷。
(二)北京高院:肯定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
在嵩旭公司案的判决作出后,北京高院在“壳牌(中国)公司与昌林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以下简称昌林公司案)中作出了相反认定。该案中,原告昌林公司是壳牌公司的经销商,诉称壳牌公司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侵害了广大经销商及用户的合法权益,壳牌公司在上诉中以双方存在仲裁约定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北京高院在该案中认可了仲裁条款的适用。北京高院遵循了合同解释的基本原则。该案中仲裁条款约定为“因本协议引起的任何争议”,上述约定包括了所有基于双方协议的权利义务关系产生、与权利行使或义务履行有关的争议。而原告提起的垄断侵权之诉同时涉及到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与双方协议约定中“特许销售权利义务”密不可分,实质上仍属于履行协议而产生的争议。 13 因此,北京高院认为双方的纠纷仍应适用该仲裁条款。
(三)实践分歧产生的问题
笔者注意到,江苏高院的嵩旭公司案和北京高院的昌林公司案的判决均在最高法院发布汇力公司案的判决之前作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垄断争议的不可仲裁性已经盖棺定论。这是因为中国并非普通法系国家,最高法院的判决并无法律上的普遍约束力,因而不能替代立法,下级法院没有义务“遵循先例”。更重要的是,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较为复杂,最高法院的判决尚未使法学界停止在该问题上的争论。因此,仍有必要对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进行研究。为此,可从中国法院在实践中的分歧所产生的问题研究开去。
对比来看,最高法院和江苏高院在两起案件中的说理体现出很大的相似性,其否定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现行法的限制。中国的反垄断法主要由行政机关加以执行或诉诸民事诉讼,但仲裁并未被规定为垄断纠纷的解决方式。第二,公共政策的考量。反垄断法具有明显的公法性质,不属于可被仲裁的范畴。第三,公共利益的影响。反垄断纠纷不仅涉及合同当事人双方,还影响到消费者、其他经销商等主体,因其公共利益性而超越了合同当事人的约定。对比来看,北京高院认可反垄断争议可以仲裁的原因则在于,双方协议体现出了当事人提交仲裁的合意。不过,北京高院对反垄断法涉及到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则没有提及。
上述分歧产生的疑问有二:
一方面,涉及众多主体的反垄断争议,是否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完全不可共存。尽管传统观点认为垄断行为不仅涉及市场竞争者之间的关系,还涉及到消费者利益等公共利益,但反垄断纠纷产生于合同双方之间,理论上应存在一定合意空间。从这个角度看,法院基于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否定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的观点还需再加审视。
另一方面,以仲裁方式解决反垄断争议在当前中国法下的可行性。尽管江苏高院和最高法院先后以中国法上没有相关规定为原因否定了反垄断纠纷,但规制上的空白恰恰也说明了没有相关规定禁止仲裁解决反垄断纠纷。故还有必要对中国的相关规定加以检视。
简言之,尽管不乏部分法院对反垄断争议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认可,中国法院对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总体上仍持否定态度,但其否定可仲裁性的理由是否正当仍存在疑问。下文将基于上述疑问,以中国法上否定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的理由为主线,探讨仲裁解决反垄断争议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三、中国法下仲裁解决反垄断争议的可行性
缺乏法律明确规定是法院否定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的首要理由。本文认为,尽管没有明确规定认可,但有关规则提供了仲裁解决反垄断争议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从可行性上看,中国法律规定并未明确排除仲裁解决反垄断纠纷的可能性。
首先,对于某项纠纷是否可以通过仲裁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分别从正面和反面进行了规定。从正面看,《仲裁法》第二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 14 从反面看,《仲裁法》第三条对不可仲裁事项作出了规定。因而,反垄断争议能否被仲裁解决,关键在于其是否落入上述可仲裁或不可仲裁的范围。
从垄断行为的类型来看,《反垄断法》共规定了四类垄断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协议、经营者集中、行政垄断。 15 这四类垄断行为并非都不具有可仲裁性。其一,横向垄断协议的当事人双方可能存在限定价格、划分市场等协议,双方地位是平等的,基于此产生的反垄断争议也落入合同纠纷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范围。与之类似,经营者集中的双方则存在并购约定,其由此产生的争议显然也落入可仲裁的范围。
其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纵向垄断协议行为中,当事人的地位则可能存在差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中,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可能会滥用其支配地位与相对方进行交易,双方可能并非是平等地位。纵向垄断协议则可能涉及供应商对经销商的固定价格、转售限制等协议,供应商同样可能存在对经销商的优势地位。因而,在上述两类行为中,有必要结合具体案情,分析当事人之间的地位是否平等,从而判断双方由此产生的争议是否属于可仲裁的范围。
其三,对于行政性垄断,此时存在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如有竞争者因此受损,其针对的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行政机关处于行政管理地位,行政行为具有公法属性,双方争议也并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并无仲裁适用空间。 16 类似地,经营者集中过程中,也涉及到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经营者集中申报的管辖权,故若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和反垄断执法机构之间产生纠纷,该类纠纷属于纵向行政管理关系的范畴,纠纷双方的地位也并不平等,此时其争议也无法通过仲裁解决。
从反面看,反垄断纠纷亦不属于仲裁的排除领域。《仲裁法》第三条规定了不能仲裁的范围,包括:“(一)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反垄断争议并不涉及第一种除外情况,对于第二种,行政性垄断和行政机关对垄断行为作出处罚的情况下,因之产生的争议可能属于行政争议,故无法以仲裁解决。但是其他类型的反垄断争议并不必然受此影响。
因而,中国现行法并未否定反垄断争议被仲裁解决的可能性,应当结合具体案情,判断争议是否产生于平等主体之间、是否属于合同纠纷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从而认定该纠纷能否通过仲裁解决。
其次,在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上,《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法院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况包括“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 17 下文第五部分将讨论,仲裁解决反垄断纠纷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并不必然矛盾,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受到侵害仍需要在个案中具体认定。因而,不宜简单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否认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
最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第十条进而对该强制性规定的范围做了界定,其中包括“(五)涉及反垄断、反倾销的”。由此来看,反垄断涉外民事关系应适用强制性规定。但上述规定并未否认仲裁的介入,仲裁庭也同样可以直接适用强制性规定。故《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同样未要求法院对反垄断纠纷的专属管辖。
从必要性上看,承认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是中国履行《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的义务。 18
根据《纽约公约》第二、三条,任何缔约国对在其他缔约国家或地区作成的仲裁裁决负有承认和执行的义务。中国是《纽约公约》的缔约国,且中国作出的是互惠保留和商事保留声明,因此只要是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如果在缔约国领土内作出了仲裁裁决,且程序上没有瑕疵,中国法院应负有承认和执行的义务。 19 而反垄断争议既有合同纠纷,也可能因为侵权产生经济纠纷,属于商事保留的范围。下文第四部分将论述,从国际趋势来看,美国及欧盟多已认可仲裁解决反垄断争议的可行性。在此情况下,如果中国法院依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的公共政策拒绝承认和执行,既有悖于国际趋势,也有可能影响跨国商事交易的发展,对中国市场产生不利影响。因而,认可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也是中国履行《纽约公约》义务的必然要求。
综上所述,中国法下反垄断争议有可仲裁的空间,这也是中国履行相关国际公约义务的要求。
四、对公共政策与可仲裁性之间矛盾的再审视
反垄断法涉及公共政策是法院否定其可仲裁性的第二条理由。本文认为,该理由也不足以成立。一方面,法院可以在事后根据公共政策审查已作出的仲裁裁决能否被承认及执行,没有必要必须在事先否定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另一方面,从公共政策的审查标准来看,其内涵也是模糊的,应当严格限制适用。
(一)公共政策影响可仲裁性的不同环节
从程序上来看,公共政策主要在两方面影响可仲裁性,一方面,公共政策会在仲裁的一开始,决定着某项争议是否可以通过仲裁解决。另一方面,公共政策会在仲裁的执行阶段,决定着某个仲裁裁决是否能够根据执行地法得到承认及执行。20 江苏高院和最高法院基于反垄断法的公法性质否定其可仲裁,实际上是在仲裁一开始就否定了争议可被仲裁解决。但这样保守的态度与国际趋势并不符合。
从美国法来看,尽管美国安全案认为反垄断争议的公共利益与仲裁存在冲突,但在随后的司法实践中,美国法院逐渐认可了争议涉及反垄断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足以否认其可仲裁性,它并不必然达到违背法院地公共政策的程度,法院应对案件进行具体分析。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85年判决的“三菱汽车公司诉索勒·克莱斯勒—普利茅斯公司一案”(以下简称三菱汽车公司案)中, 21 原告三菱汽车公司(Mitsubishi Motors Corp.)因被告索勒·克莱斯勒—普利茅斯公司(Soler Chrysler-Plymouth, Inc.,以下简称索勒公司)销售合同发生争议,三菱汽车公司在日本提起仲裁,而索勒公司则提出反诉。三菱汽车公司的上诉请求是“考虑美国法院是否应该强制一项国际性协议中产生的反垄断诉求进行仲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反垄断争议的复杂性或涉及公共利益本身并不足以否定其可以仲裁解决,既然法律规定了私人可以在反垄断法下得到救济,如果不能通过仲裁来解决垄断纠纷,反而会增加争议解决的不确定程度。若裁决结果真的违背了公共政策,法院仍可以拒绝执行。22 可见,法院拒绝采用宽泛的公共政策在仲裁开始阶段就排除一切反垄断争议。而是肯定私人也可以依据反垄断法受到保护,是对公共政策更为严格的限定。
并且,该案中法院还区分了国际争议和国内争议,在国际争议中,应当考虑到“国际礼让、尊重外国以及国际法院的能力,以及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可预见性”,从而“将支持仲裁的联邦政策置于不可仲裁的国内法之上”。 23 而在该案后,美国法院又通过“考得曼电子公司诉JBL消费产品公司案”肯定了纯粹的国内反垄断争议同样可以通过仲裁解决。24 可见,公共政策并非否定可仲裁性的决定性因素,在仲裁裁决作出后依据公共政策审查裁决能否被承认及执行,应当是更为可取的审查方式。
更进一步,从公共政策的内涵来看,江苏高院和最高法院都未在判决中对公共政策给出具体的解释,现行法的规定更多集中于审查仲裁裁决的公共政策,下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二)内含模糊的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的内涵范围届定着法院和仲裁庭管辖的边界。公共政策通常被理解为与国家、社会利益有关的重大事项,但其具体含义并无明确统一的规定,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理解。25 这就给公共政策的适用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各国法院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作出不同解释。在裁决作出地被认为不违反公共政策,在裁决执行地就可能相反。如果法院坚持适用广范围的公共政策,就可能导致许多争议无法通过仲裁解决。从中国法院适用公共政策的标准来看,最高法院曾试图采用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方法对公共政策予以界定。肯定性标准主要包括法律基本原则、社会根本利益和善良风俗;否定性标准则包括仲裁结果显失公平、争议事项不可仲裁等。26 但是,这些标准本身就存在解释的空间,在适用时标准也并不统一。
因此,考虑到公共政策内容的模糊性,应当严格限制公共政策的适用。法院只有证明具体的反垄断争议真的达到了足以违背公共政策的程度,才能否认其可仲裁性。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后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即使涉及到垄断行为,该仲裁条款所针对的也是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不会涉及到公共利益。如果当事人因垄断行为受到经济损失,据此与垄断行为人约定仲裁,更是当事人救济权利的正当手段,与公共政策无涉。而对于法院担心的垄断行为所造成的公共利益损失,仲裁并没有排除行政机关依职权对垄断行为人进行处罚,这种处罚本身就带有补偿公共利益的性质。《反垄断法》在授权反垄断执法机关查处违法行为的同时,也在第五十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可见,公益补偿和私益救济同时得到承认,通过仲裁解决私人纠纷并不必然导致对公共政策的违反。
从国际趋势来看,公共政策的范围也不断趋于缩小。传统上,公共政策是各国不信任仲裁的理由,因为争议涉及国家社会利益,不允许带有民间性质的仲裁来解决,而要交给国家司法机关专属管辖。27 但随着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的普及,法院对公共政策的适用变得越来越谨慎。例如,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帕森案中指出“只有在外国仲裁裁决的执行会违反法院所在国最基本的道德和正义理念的情况下,才能以公共政策为依据拒绝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认为只有那些“触及基本、核心道德和正义问题的方面”,才能适用公共政策拒绝执行。在欧洲,瑞士联邦最高法院裁定违背公共政策是指“以无法忍受的方式”违反瑞士正义概念的裁决,德国法院则将规范“影响到德国公众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基础”作为判断标准。28 因此,只有当反垄断争议达到了这些标准,构成了对最基本道德准则的违背时,才有可能因涉及公共政策而被排除出仲裁范围。并且,法院也在区分国际公共政策和国内公共政策,在国际争议中,考虑到国际礼让和国际贸易的需求,更不应该用国内的公共政策来阻碍仲裁 29。 这也在上文讨论的三菱汽车公司案中得到体现。 30
最后,从结果上看,赋予反垄断争议以可仲裁性,并不必然与公共政策相冲突,反而可能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公共政策。仲裁作为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专业、高效、保密等特点,具备专业知识水平的仲裁员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对争议作出裁断,抑制垄断企业的违法行为,恢复正常的市场秩序,甚至可能比诉讼更加高效方便,这当然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
综上所述,在公共政策的含义本身模糊的情况下,其适用范围应被严格限定,法院不应在仲裁开始阶段就基于公共政策否定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而可在通过仲裁裁决作出后的司法审查中确保相关裁决与公共政策相互协调。
五、公共利益与意思自治的冲突与调和
法院否定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的第三条理由,是垄断行为的认定涉及到其他主体,超越了当事人之间意思自治的范围。本文认为,该理由同样不能成立,原因在于,第一,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或其他财产权益纷属于可仲裁范围,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应得到尊重。其二,反垄断纠纷涉及的公共利益也可以在仲裁中得到考量,且仲裁庭仅在当事人约定的范围内作出裁决,不涉及到对其他主体权利的处分。即便裁决有不当之处,也可通过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进行把关。因而,涉及公共利益也不足以否定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
(一)反垄断争议中意思自治的有效性
意思自治是仲裁的基石,当事人之间有效的仲裁协议授予了仲裁庭管辖权的来源,也约束着仲裁庭对裁判权的行使。如前所析,根据《仲裁法》的规定,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因而,反垄断纠纷可仲裁的起点,是当事人有效的约定。
一方面,当事人约定的有效性应结合垄断行为的具体类型判断。对于横向垄断行为、经营者集中两类情形,其符合当事人地位平等、合同纠纷或财产权益纠纷的条件,落入可仲裁的范围。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纵向垄断协议,则需要结合案情,分析当事人之间的地位是否平等,判断其是否属于可仲裁的范围。行政性垄断则不可仲裁。
另一方面,当事人约定的有效性应结合双方地位、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判断。若当事人之间因地位不对等、意思表示不真实等作出了与实际意思不符的约定,这样的“意思自治”显然是不能被尊重的。 31 例如,在一方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反垄断争议里,该方可能利用其在交易中的优势地位,强制性要求对方与自己签署协议或进行交易,这种情况下,需要考虑双方约定的仲裁条款是否还是真实意思的体现。
本文认为,不宜简单以市场支配地位的存在否认双方在仲裁协议中的意思表示。一方面,市场支配地位的存在对合同的影响主要是表现在主合同条款上,例如一方胁迫另一方以高价购买商品、或者强制对方交易。而仲裁条款是双方协议解决争议的方式,处于弱势的一方可能恰恰以此作为自己未来寻求救济的方式。而且根据仲裁协议独立性的原则,仲裁协议独立存在,不受合同是否有效的影响,主合同意思表示即便不真实,也不会影响到仲裁协议的效力。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在仲裁协议中意思表示不真实,则法院应可以认定仲裁协议无效而行使管辖权。但若无上述情形,且符合可仲裁性的其他条件,则应肯定当事人的约定。
由此来看,北京高院在昌林公司案中,基于双方有效的仲裁协议,认定该案纠纷落入仲裁协议范围、从而应受仲裁管辖,32 正是尊重了双方的意思自治,较为合理。
(二)公共利益不足以否定可仲裁性
意思自治并非没有边界,社会公共利益便是限制之一。33 社会公共利益本身是个抽象的概念,其代表着社会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非某些个体的利益,34 体现出社会最根本的价值取向。35 例如,美国安全案中,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就认为,仲裁作为解决私人纠纷的方式,并不适宜解决涉及公共利益的反垄断案件。36 江苏高院及最高法院的说理也认为,若一方诉请不仅涉及到争议双方的纠纷,还关涉到其他主体的利益,对该事项就不能仅仅在当事人之间解决。37 这样的观点可能过于武断。
不可否认,在反垄断争议的解决中,垄断行为的认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配置等,都有可能涉及到其他竞争者、经销商、消费者等群体,不再仅局限于约定仲裁条款的当事人之间。由此来看,仲裁庭解决此类纠纷的潜在问题可能有两方面:第一,仲裁庭的裁决可能处置了非合同缔约方的权利义务,第二,仲裁庭在作出裁决的过程中,可能没有考虑到其他主体的利益。本文认为,上述两方面的问题都可得到解决,因而不能成为否定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的理由。
一方面,对于仲裁庭裁决的范围。根据《仲裁法》及《民事诉讼法》,仲裁的进行应当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解决纠纷。 38 若仲裁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相关裁决可被 39 撤销或不予执行。40 由此可见,仲裁庭需要基于当事人的仲裁协议解决纠纷,处理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能超出该协议的范围解决纠纷。并且,仲裁庭对缔约一方的救济,并不影响其他利益相关方基于垄断者的不当行为通过其他方式主张权利。即便有裁决与仲裁协议不符的情况,法院的司法审查也将发挥把关作用,可以在事后否定其效力。
另一方面,对于仲裁庭在裁决中的考量。仲裁作为专业的纠纷解决方式,也有专业能力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考虑公共利益。例如,仲裁机构在聘任仲裁员时,也会聘任具有反垄断专长的仲裁员。如果仲裁庭在裁决中合理考量了其他相关方的利益,同时仅对双方权利义务作出裁决,这样的仲裁结果并无不当之处,应得到承认及执行。如果仲裁庭在裁决中没有考虑到公共利益,法院可以通过对裁决的司法审查,撤销违反公共利益的裁决。
此外,还应考虑到反垄断纠纷也有民事解决路径。《反垄断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三菱汽车公司案中所指出的,法律赋予了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从垄断者获得赔偿的权利,而仲裁恰恰是当事人实现这一权利的重要途径。41 这也正是北京高院在壳牌公司与昌林公司纠纷案中的观点:在当事人约定了仲裁事项的情况下,基于双方协议的有关争议都应属于仲裁事项,这是双方合意处置的范畴。42
与上述做法相比,若法院直接在事前否定了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反而会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商事主体难以对双方约定的执行形成稳定预期,这可能进一步影响其是否进行商事活动的判断。另一方面,全盘否定合同双方之间的仲裁约定,也有可能变相鼓励一方当事人在纠纷发生时否认其原先的意思表示,而是借助选择法院实现利益诉求,43 这也有悖于商事交易的诚信原则和稳定性要求。
综上所述,反垄断争议尽管涉及公共利益,但这不能成为否认仲裁解决反垄断争议的充分理由。更为妥当的做法是,尊重当事人的约定、允许当事人在适当范围内通过仲裁解决反垄断纠纷,在执行仲裁裁决时由法院结合个案具体情况审查仲裁裁决是否违反公共利益。
六、反垄断争议可仲裁性的司法介入路径
根据前文所述,对于反垄断争议,应当区分不同类型,判断是否可以通过仲裁形式解决:对于因行政垄断造成的争议,仲裁并无介入空间;而对于平等主体之间因垄断行为产生的争议,仲裁解决在现行法下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反垄断法涉及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也都不足以否定相关争议的可仲裁性。在具体实施的层面上,由于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由司法机关来作出判断,故还有必要明确司法介入这一问题的具体路径。司法机关的介入有两个可能的时点:其一是在仲裁刚开始之时,如果一方当事人提交仲裁,另一方可能否认仲裁庭的管辖权并在法院起诉。其二是仲裁裁决作出后,涉及法院对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在仲裁刚开始之时,如果一方当事人对仲裁有异议,可以提交法院作出判断,问题在于,如何处理仲裁委员会自行裁定管辖权和人民法院裁定管辖权的关系?《仲裁法》第二十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由此可见,法律并不否认仲裁庭的自裁管辖权,但法院应对可仲裁性拥有最终管辖权。考虑到反垄断争议涉及公共政策,可能属于司法管辖权的范畴,由法院而非仲裁庭来对之作出判断也更为合适。
在仲裁裁决作出后,涉及到法院对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首先,法院可依职权直接审查涉及反垄断争议的裁决是否因违背公共政策而应拒绝承认和执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对于经认定违反公共政策、或者不能以仲裁解决的争议事项,法院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这两处规定的措辞都赋予了法院直接依职权审查的权利。从实质上看,公共政策关涉法院地最根本的道德准则,法院也应有权直接审查。 44
其次,在审查标准上,存在最高标准、最低标准和平衡标准之分。所谓最高标准,是指法院可以对仲裁庭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都重新予以审查,这在2005年荷兰海牙上诉法院判决的“市场显示器国际有限公司诉范拉尔特广告有限公司案” 45 中得到体现。海牙上诉法院审理后认为,当事人存在限制竞争行为且不属于豁免情形,协议中关于限制竞争的规定违反了欧盟竞争法,导致整个独家许可协议无效,并最终依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的公共政策条款拒绝执行美国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 46
与之相对,最低标准则是指法院对仲裁庭认定的事实一般不重新审查,对如何确定与适用法律也不予审查,只有当仲裁庭解释法院地的公共政策存在错误,或者当事人提出的新证据足以影响仲裁庭改变裁决的情况下,法院才应对仲裁裁决重新审查。该标准在巴黎上诉法院2004年判决的“泰雷兹公司诉欧洲导弹公司案”47 中被适用。该案中,泰雷兹公司(Thales Air Defense)以案涉许可规定违反欧盟竞争法而无效为理由,请求法院撤销该仲裁裁决,但这一申辩并未在仲裁进行过程中提出。法院认为,尽管请求撤销裁决不是毫无道理,但这要求对仲裁裁决进行实质审查,法国法律并不允许这样做,并且,仲裁裁决只有违反竞争法达到明显的程度才能构成撤销的理由。最后,法院尊重了仲裁庭的裁决。 48
对比来看,在最高标准下,法院实际上对案件进行了重新审理,与仲裁一裁终局的原则相违背。在最低标准下,法院尽管尊重了仲裁庭的决定,但其适用过于宽松的标准,又与其依职权认定是否违背公共政策有相悖之处。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了平衡标准,即法院应根据案涉垄断行为的类型、仲裁程序等因素综合确定是否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这也是三菱汽车公司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持的立场。本文亦认可以平衡标准作为法院审查相应仲裁裁决的合理标准。
最后,在实质上,还需明确仲裁裁决足以违反公共政策的事实情形。如前所述,笼统地根据公共政策否定仲裁可行性的做法难以站得住脚,还应当根据案涉反垄断争议的具体类型进行判断。在具体适用中,公共政策的范围应被严格限定,并在跨国反垄断争议中考虑到国际礼让等因素。若相应仲裁裁决没有其他违背公共政策情形的情况,不宜仅仅因其裁定了反垄断争议,就认定其不可被承认及执行。 49
结语
传统上,经营者之间的反垄断争议因涉及到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被认为与可仲裁性之间存在矛盾。中国法院也对反垄断争议持不可仲裁的态度。最高法院及江苏高院在各自的裁定中,对反垄断案件不可仲裁给出了三点原因:缺乏明确规定认可;反垄断争议具有公共政策性;案件涉及公共利益。然而细加审视可以发现,反垄断争议与仲裁之间并非不可共存。
首先,从法律规定上看,承认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没有超出《仲裁法》所规定的可仲裁范围,也是中国作为《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应当履行的条约义务。其次,反垄断争议并不一定违反公共政策,因合同纠纷产生的反垄断争议由当事人自行处理,因垄断行为遭受经济损失而寻求仲裁也是当事人理应得到的救济。公共政策的含义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避免滥用公共政策而过分排除仲裁庭的管辖权。再次,反垄断争议中当事人有效的意思自治应得到尊重,仲裁庭有能力在裁决过程中考量公共利益,也应仅就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裁断。最后,在司法介入路径上,法院在仲裁刚开始之时对争议是否可以仲裁拥有最终管辖权,在裁决作出后则可依职权对反垄断争议是否违背公共政策予以审查,但应严格限制公共政策适用,并根据具体案件事实判断。
尽管否定了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对于仲裁解决案件中所涉垄断行为对公共利益造成的具体不利影响,法院却缺乏实质和具体的分析。事实上,中国法律中对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也确实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可资参考。在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外国法院所承认的背景下,建议中国也能够通过最高法院进行司法解释、或者至少是有法院对该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等方式,对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予以阐明,明确涉及部分垄断行为的纠纷是可以被仲裁的。这对于中国商事仲裁的发展、《纽约公约》义务的履行以及商事交易的进行,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 朱子琳,经济法学硕士,现就职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1.杜新丽:《从比较法的角度论我国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5期。
2.See James Bridgeman, “The Arbitrability of Competition Law Disputes”, European Business Law Review, 2008, p.147.
3.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民辖终44号民事裁定书。
4.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知民辖终字第72号民事裁定书。江苏高院在该案中认定,反垄断争议因涉及公共利益,不具有可仲裁性。
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47号民事裁定书。
6.王先林:《反垄断法的基本性质和特征》,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1期。
7.宋连斌:《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
8.其中可处分性是指争议事项可以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处分,属于双方意思自治的范畴;商事性是指争议事项与商事关系有关,涉及商业交易;经济利益则是指争议涉及到当事人的经济权益。参见林燕萍:《反垄断争议的仲裁解决路径》,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8-49页。另见张艾青:《国际商事仲裁中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23页。参见杜新丽:《从比较法的角度论我国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5期。
9.See American Safety Equipment Corp. v. J.P. Maguire & Co., 391 F.2d 821.
10.See American Safety Equipment Corp. v. J.P. Maguire & Co., 391 F.2d 821.参见林燕萍:《反垄断争议的仲裁解决路径》,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3页。
11.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知民辖终字第72号民事裁定书。
1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47号民事裁定书。
13.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民辖终44号民事裁定书。
14.《仲裁法》第二条 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
15.参见《反垄断法》第十三条到第三十七条。
16.参见丁国峰:《美国反垄断法可仲裁性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0年第11期。
17.《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 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
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
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
第二百七十四条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
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18.杜新丽:《从比较法的角度论我国反垄断争议的可仲裁性》,载《比较法研究》 2008年第5期。
1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1987年4月10日法(经)发〔1987〕5号),第一、二条。
20.See Nigel Blackby et al., Redfern and Hunter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655.
21.See Mitsubishi Motors Corp. v. Soler Chrysler-Plymouth, Inc., 105 S. Ct. 3346.
22.参见林燕萍:《反垄断争议的仲裁解决路径》,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8-102页。
23.参见林燕萍:《反垄断争议的仲裁解决路径》,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页。
24.See Kotam Electronics, Inc. v. JBL Consumer Products, Inc., 93 F.3d 724.
25.See Nigel Blackby et al., Redfern and Hunter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656.
26.参见何其生:《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中的公共政策》,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27.参见张艾青:《国际商事仲裁中公共政策事项的可仲裁性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6期。
28.See UNCITRAL Secretariat Guide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New York, 1958), 2016 ed., pp.240-242.
29.See UNCITRAL Secretariat Guide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New York, 1958), 2016 ed., pp.243-244.
30.See Mitsubishi Motors Corp. v. Soler Chrysler-Plymouth, Inc., 105 S. Ct. 3346, at 3355.参见林燕萍:《反垄断争议的仲裁解决路径》,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03页。
31.类似说理也体现在三菱汽车公司案中。See Mitsubishi Motors Corp. v. Soler Chrysler-Plymouth, Inc., 105 S. Ct. 3346, at 3354.
32.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民辖终44号民事裁定书。
33.参见饶传平、焦洪涛:《可仲裁性理论探微》,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34.参见王景斌:《论公共利益之界定——一个公法学基石性范畴的法理学分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1期。
35.参见李梦园、宋连斌:《论社会公共利益与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对我国法院若干司法实践的分析》,载《北京仲裁》2006年第1期。
36.See American Safety Equipment Corp. v. J.P. Maguire & Co., 391 F.2d 821.
37.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知民辖终字第72号民事裁定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辖终47号民事裁定书。
38.《仲裁法》第七条 仲裁应当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地解决纠纷。
39.《仲裁法》第五十八条 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
(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
……
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
40.《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
(四)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41.See Mitsubishi Motors Corp. v. Soler Chrysler-Plymouth, Inc., 105 S. Ct. 3346, at 3357.
42.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京民辖终44号民事裁定书。
43.参见黄伟、尹蓓、周雯:《中国反垄断实践实务问题与案例解析》,载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https://law.wkinfo.com.cn/commentary/detail/MTU1NTM0Nw%3D%3D?searchId=785435f3233e4af0b6b66a63cd987bf2&index=1&q=%E5%8F%8D%E5%9E%84%E6%96%AD%E4%BA%89%E8%AE%AE%20%E5%8F%AF%E4%BB%B2%E8%A3%81%E6%80%A7&title=2.2.%20%E5%8F%8D%E5%9E%84%E6%96%AD%E6%B0%91%E4%BA%8,2021年8月1日最后访问。
44.See UNCITRAL Secretariat Guide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New York, 1958), 2016 ed., pp.258-259.
45.See Court of Appeal of The Hague, Marketing Displays International Inc., v. VR Van RaalteReclame BV, Case No. 04/694 and 04/695.
46.参见林燕萍:《反垄断争议的仲裁解决路径》,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29-136页。
47.See La S.A. Thalès Air Defense v. Le G.I.E. Euromissile and La S.A. EADS France and La socie’ te’ EADS Deutschland GmbH, Case 2002/19606, decision of 18 November 2004.
48.参见林燕萍:《反垄断争议的仲裁解决路径》,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29-136页。
49.参见何其生:《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审查中的公共政策》,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
(本文原载《仲裁与法律》第14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