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宗劼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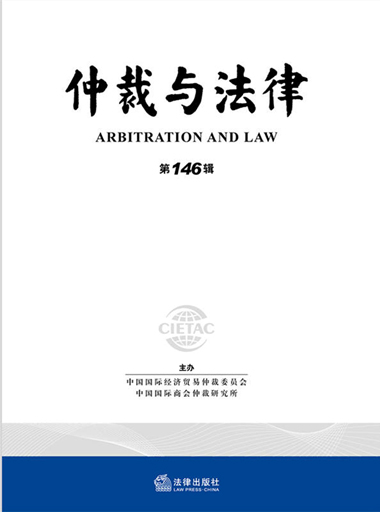
摘要:ICSID仲裁裁决借由《华盛顿公约》所构建的承认与执行机制被评价为是一套“自足的”制度,其仲裁裁决的执行依靠的是败诉东道国政府的自觉履行,《华盛顿公约》并未规定任何强制执行程序;对于败诉东道国拒不执行ICSID仲裁裁决的情况,《华盛顿公约》也未规定十分行之有效的惩罚机制。ICSID仲裁中的败诉东道国完全可以利用《华盛顿公约》第55条赋予的国家主权豁免制度逃避责任。因此,ICSID仲裁裁决的执行受制于国家主权豁免制度而面临着现实和潜在的困境。聚焦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机制却不尽完善,具体表现为中国现有的仲裁司法审查制度将有可能阻却涉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为保障涉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获得承认与执行,需完善中国的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机制。一方面,中国应当在不违反《华盛顿公约》精神的基础上建立适合中国的ICSID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与制定相关国家主权豁免立法。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司法互惠关系探索与他国建立更多的国际投资仲裁互惠关系,以保障通过其他非ICSID仲裁方式解决的国际投资争议解决结果(如判决)获得承认与执行。
关键词:ICSID仲裁裁决执行困境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机制 涉华国际投资仲裁 “一带一路”
一、引言
传统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简称“ISDS机制”)多为政治协商、外交保护和诉诸武力等,但在二战后,人们意识到传统方式不能满足国际社会和平共同发展的需求。在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繁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大量资本需向外寻找市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努力发展经济,急需资金。在这一国际投资大发展时期的背景下,为了能够弥补传统的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方法与双边条约出现的技术上与程序上的“缺陷”,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在世界银行的积极倡导和主持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于1965年共同制订和缔结了《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以下简称《华盛顿公约》),并据此设立了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以下简称ICSID)。由《华盛顿公约》创立的ICSID仲裁机制一方面反对将国际投资争议政治化,反对以外交保护和武力索债作为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的方式,另一方面也不赞成由东道国排他性地管辖此类争议,而是主张运用中立的国际仲裁方式解决争议。2 ICSID作为目前最“权威”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在国际投资大发展时期以国家和个人投资者之间平衡点的姿态解决了许多国际投资争议。但随着世界经济政治的进一步发展,ICSID机制的实践面临越来越多的困境,其权威性愈发受到挑战。
从裁决既判力和执行力的角度来看,ICSID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是ICSID巩固其权威性最重要的一环。现代国际投资仲裁大都根据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以下简称BIT)发起,而ICSID所作出的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则规定于《华盛顿公约》之中,非ICSID作出的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则一般通过争议双方事前约定或通过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进行,但由于ICSID仲裁机制是ISDS机制中被广泛运用的,故本文将主要讨论ICSID以及《华盛顿公约》所共同构建的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问题。伴随而来的问题主要包括现有ICSID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机制为何?ICSID仲裁裁决的实际执行状况如何以及是否存在障碍?而从中国实际出发,涉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则更应受到重视。因此,本文将从ICSID现有机制出发,分析ICSID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机制及其现状,并探讨导致其执行困难的原因,并结合中国实际讨论涉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相关问题及制度构想。
二、ICSID仲裁裁决的执行困境概述
ICSID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其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华盛顿公约》所构建的ICSID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虽然被评价为是一套“自足的”制度,但受制于国家主权豁免制度,其承认与执行机制面临着现实和潜在的困境。本部分在分析ICSID的承认与执行机制的基础上,对ICSID仲裁裁决的执行困境进行论述。
(一)ICSID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机制
ICSID仲裁机制的承认与执行制度规定在《华盛顿公约》第53至55条中,形成了一套简单、自动且自足的体系。简言之,《华盛顿公约》第53条规定了缔约国不得逾越公约内机制推翻ICSID仲裁裁决的效力;第54条要求缔约国负有无条件承认ICSID仲裁裁决并予以执行的义务;第55条则留下国家主权豁免制度在ICSID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中的适用空间。上述三条规定构成一套完整的ICSID承认与执行制度,主要体现在三条款之间以及与《华盛顿公约》其他条款的相互作用之中。
1. ICSID仲裁裁决的承认机制
《华盛顿公约》的第53条直接、明确地规定了ICSID仲裁裁决的承认机制。同时,《华盛顿公约》第53条与第25条和第54条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仲裁裁决承认机制。
首先,《华盛顿公约》第53条规定:“裁决对双方有约束力。不得进行任何上诉或采取任何其他除本公约规定外的补救办法。除依照本公约有关规定予以停止执行的情况外,每一方应遵守和履行裁决的规定。”第53条明确规定ICSID仲裁裁决对争议双方具有约束力,且不得通过逾越《华盛顿公约》所规定的机制进行上诉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手段,这样的规定进一步排除了其他非和平、非良性“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以下简称“ISDS机制”)的适用空间。与第53条配套的是《华盛顿公约》第25条规定的ICSID管辖权条款,该条规定:“中心的管辖适用于缔约国(或缔约国指派到中心的该国的任何组成部分或机构)和另一缔约国国民之间直接因投资而产生的任何法律争端,而该项争端经双方书面同意提交给中心。当双方表示同意后,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撤销其同意。”换言之,当缔约国同意将投资者与国家间争议提交ICSID解决时,就已明示放弃了主权国家享有的管辖豁免,至于争议过程中的管辖权异议往往是针对案件事实本身是否属于ICSID仲裁制度中的可仲裁事由而进行的讨论。而当ICISD仲裁庭作出裁判后,借由第53条的规定,其裁判即原始地取得了对双方的约束力。两相作用下,ICSID仲裁裁决获得了既判力,也为进一步的承认机制打下基础。
其次,《华盛顿公约》第54条第1款规定:“每一缔约国应承认本公约作出的裁决具有约束力,并在其领土内履行该裁决所加的财政义务,正如该裁决是该国法院的最后判决一样。具有联邦宪法的缔约国可以在联邦法院或通过该法院执行该裁决,并可规定联邦法院应把该裁决视为其组成的一邦的法院作出的最后判决。”第54条第1款明确要求所有缔约国承认ICSID所作出的裁决具有约束力,将其裁判的效力与缔约国国内法院终审裁判的约束力划上等号,并要求所有缔约国在其领土范围内履行ICSID仲裁裁决所附加的财政义务,这使得加入《华盛顿公约》的主权国家不得不承认ICSID所做裁判具有权威性。而第54条第2款规定:“要求在一缔约国领土内予以承认或执行的一方,应向该缔约国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主管法院或其他机构提供经秘书长核证无误的该裁决的副本一份。每一缔约国应将为此目的而指定的主管法院或其他机构以及随后关于此项指定的任何变动通知秘书长。”在《华盛顿公约》第54条内部的相互作用下,强制赋予了缔约国无条件承认ICSID仲裁裁决的义务以及告知ICSID秘书长有关裁决承认与执行情况的告知义务,使通过第53条获得的既判力得到深化。
综上,ICSID仲裁裁决的承认机制通过《华盛顿公约》第53条和第25条的相互作用以及第54条规定的作用下,使得缔约国负有无条件承认ICSID仲裁裁决既判力的义务,并同时排除了缔约国管辖豁免和国内司法干预的适用空间,一方面体现了ICSID仲裁这一特殊形式的国际商事仲裁在其裁决承认阶段也仍具备国际商事仲裁的内核,即契约性,另一方面也满足并体现了ICSID机制创设的目的和宗旨,是一套完整的承认机制。
2. ICSID仲裁裁决的执行机制
如前文所述,《华盛顿公约》使缔约国负有无条件承认其裁决的义务,为ICSID仲裁裁决的执行打下基础。但《华盛顿公约》第53至55条所规定的执行机制却缺乏了执行力的保证,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首先,《华盛顿公约》并未规定完整的强制执行程序,第54条所规定的执行义务仅限于金钱义务,如支付赔偿金及利息,而对于非金钱义务则仍要求缔约国自觉履行裁决。其次,《华盛顿公约》第55条规定:“第54条的规定不得解释为背离任何缔约国现行的关于免除该国或任何外国予以执行的法律。”因为国家主权豁免制度仍可适用于ICSID仲裁裁决的执行阶段,所以可能导致ICSID仲裁裁决的执行申请人还需再进行一轮争议阶段,甚至有可能使有利于自身的裁决最终无法得到执行。最后,《华盛顿公约》第27条所规定的不遵守或不执行ICSID裁决的法律后果的适用空间和可能性过窄 3,加大了败诉东道国拖延执行或不执行ICSID仲裁裁决的可能性。在上述条款的综合作用下,胜诉投资者仅能通过第54条的规定获得金钱赔偿,但这一获赔还可能受到国家主权豁免制度的阻碍。
可见,ICISD仲裁裁决的执行机制虽看似健全,但实际上是缺乏执行力保证的。从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关系来看,二者本就实力悬殊,投资者在通过ICSID机制获得了与东道国平等对话解决争议的渠道并获得了有利于自身的裁决结果后,却还需要通过东道国国内相关司法途径实现实际利益,这本身就不能体现仲裁的契约性。所以《华盛顿公约》要求缔约国自觉履行裁判,并且排除了公共秩序保留,不允许缔约国对承认和执行ICSID仲裁裁决作出任何保留,这么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执行力。但《华盛顿公约》仅赋予了投资者申请强制执行裁决中金钱义务的权利,使得ICSID仲裁裁决的执行申请人可申请强制执行的范围大大缩水,而投资利益本身就是一个大命题,有时非金钱义务所带给投资者的效益是远远大于金钱义务的 4;与此同时,《华盛顿公约》又留下了国家主权豁免制度在执行阶段的适用空间,使得东道国完全有可能通过国内有关国家豁免的司法制度加以规避自身所负的执行义务,甚至借此制度报复胜诉的投资者;最后,当东道国拒不遵守和执行裁决后,《华盛顿公约》又赋予投资者母国恢复并适用外交保护途径以保护母国投资者的非良性ISDS机制,这本质上违背了《华盛顿公约》序言部分所确立的和平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精神,原本所搭建的平等对话桥梁因此失去最后一块制度保障。在ICSID仲裁裁决的执行阶段,任何现有的承认和执行ICSID裁决的国际制度都没有为执行申请人提供任何简单有效的方法。
综上所述,将ICSID仲裁的承认与执行机制区分来看,其承认机制是一套完整的、符合《华盛顿公约》精神且彰显商事仲裁契约性的制度,但其执行制度缺乏有力的执行保障。而ICSID仲裁裁决已形成了“自足的”(self-contained)承认机制,但执行机制却受到了国家主权豁免制度的挑战和阻碍。
(二)国家主权豁免制度导致的执行困境
如前文所述,在ICSID仲裁中败诉的东道国往往会自觉履行执行的义务,但国家主权豁免制度是胜诉投资者申请执行ICSID仲裁裁决的障碍,特别是如何寻获不享有执行豁免的东道国财产。本文将引用AIG私募股权有限公司诉哈萨克斯坦(AIG Capital Partners, Inc., CJSC Tema Real Estate Company v. Kazakhstan, ICSID Case No. ARB/01/6,以下简称AIG诉哈萨克斯坦)以及利比里亚东部木材公司诉利比里亚(Liberian Eastern Timber Corporation v. Republic of Liberia, ICSID Case No. ARB/83/2,以下简称LETCO诉利比里亚)两案阐述实践中国家主权豁免制度对ICSID裁决执行造成的阻碍,即在实践中投资者难以定位并证明申请执行的财产属于东道国的财产。
1. 难以寻获东道国可被执行财产
在LETCO诉利比里亚一案中 5,法国LETCO公司在1986年3月31日获得有利于自己的ICSID仲裁裁决后,由于利比里亚未自觉执行相关裁决,LETCO公司遂在美国纽约南部地区法院请求强制执行利比里亚在美国的资产。6
首先,LETCO公司获得了美国纽约南部地区法院承认并执行相关裁决的裁定,但利比里亚很快提出了国家主权豁免请求。美国纽约南部地区法院遂根据美国《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并通过《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第1610条认定LETCO公司申请执行的利比里亚在美国的资产不可执行,因其是属于用于利比里亚主权职能的税收收入,而不是用于商业职能的财产,于是美国纽约南部地区法院撤销了对相关财产的执行命令。其次,LETCO公司又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院请求执行利比里亚位于华盛顿的大使馆的银行账户中的资产,但最终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院又撤销了相关查封命令,理由是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美国《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的规定,上述相关账户中的资金具有公共性质且大使馆银行帐户因享有外交豁免权是免予查封扣押的。7
由LETCO诉利比里亚一案的执行过程可以看出,美国在其国内有关国家主权豁免的法律中都注重对国家资产是否用于“商业活动”(Commercial Activity) 8 的审查,但因证明执行财产用于“商业活动”的举证责任在执行申请人一方,故导致的后果是ICSID裁决的执行申请人在有相关国家主权豁免制度立法的国家难以找到合适且合格的被申请执行东道国资产。ICSID仲裁裁决的执行申请人只能像LETCO公司一样不断寻找相关资产,再予以证明其是否属于可被执行的财产,徒增执行申请人的司法成本,而在缺乏相关国家主权豁免制度立法的国家则更加难以实际执行败诉东道国的资产以填补遭受的损失。美国《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对豁免的例外并未有明晰的界定,更未对“商业活动”进行认定,但如下述AIG公司诉哈萨克斯坦一案一样,即使申请执行地有相关的立法或司法对“商业活动”进行了规定,执行申请人也难以寻获符合标准的东道国财产。
2. 难以界定东道国财产的属性
在AIG公司诉哈萨克斯坦一案中 9,美国AIG公司实际控股的CJSC Tema房地产公司于1999年12月13日与哈萨克斯坦投资局签订房地产建设合同。在完成大部分建设后,哈萨克斯坦发布停止施工的命令。CJSC Tema房地产公司遂无奈于2000年6月16日以不可抗力为由,解除了其与下游建筑承包商的施工合同并支付了违约金。为解决争议,AIG公司2001年6月4日向ICSID发起针对哈萨克斯坦的国际投资仲裁。本案仲裁庭审议后,裁定哈萨克斯坦政府部门的行为构成对投资者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投资的征收,哈萨克斯坦政府应当向投资者支付非法征收赔偿金以及预期利益损失。随后AIG公司试图在英国执行ICSID裁决,并成功在英国登记了该裁决的执行请求。但AIG公司试图将第三方银行以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的名义在英国持有的,且利益归属于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的现金和证券作为执行标的。AIG公司认为,上述资产是哈萨克斯坦的资产因而获得了这些帐户的临时扣押命令,但哈萨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随即提出适用国家主权豁免制度。 10
英国法院在其分析过程中认为,如果被认定为是用于“商业活动”的财产则不属于豁免的例外,是可以被执行的国家财产。因此,英国法院在对主权国家财产进行强制执行时需要“确定一国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所持有的某一特定资产,在相关的时间内,是否正在使用或打算用于商业活动”。11 法院在分析后确定,对于第三方银行以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的名义在英国持有的,且利益归属于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的现金和证券,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对其享有相关的专属合同权利,因此,“在所有情况下,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的财产不应被视为正在使用或打算用于商业活动”。12 故法院作出裁定认为,上述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的财产受到英国法院完全执行豁免的保护,法院随即解除了临时扣押令。
上述案例中,英国法院根据其《1978年国家豁免法》以及国家主权豁免制度的一般规则的规定,其审查最为重要的标准是申请执行的标的是否属于国家资产以及是否正在用于或打算用于“商业活动”。正因如此,证明申请执行的财产是否用于“商业活动”则成了投资者所负担的举证责任,而投资者难以举证证明申请执行的财产属于东道国用于“商业活动”的财产。并且由于一国法院自然地不愿意侵犯外国主权,故申请执行地法院也不愿在实际的案件中清晰界定相关判断标准以供投资者参考辅证。
综上,在申请执行ICISD仲裁裁决的过程中,一旦东道国运用国家权豁免制度阻碍执行,随即产生的就是申请执行财产的属性问题。一方面,申请执行地法院不愿干涉他国主权,故不愿作出相关属性判断的标准;另一方面,申请执行人承担了相关举证责任,但却没有相关依据予以辅证。两相作用下,ICSID仲裁裁决的执行因难以界定东道国财产的属性而受阻。
总体而言,在国际法层面,有关国家豁免最重要的两个条约是2004年《联合国豁免公约》和1972年《欧洲国家豁免公约》,但《联合国豁免公约》至今仍未生效,而《欧洲国家豁免公约》缔约国数量有限,所以两大公约的实际影响力非常有限。而在国内法层面,国家豁免立法在英美法系的英国、美国等国表现为成文立法,而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均没有国家豁免的专门立法,需要从案例中梳理该国的国家豁免规则。在国内立法中,美国《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和英国《1978年国家豁免法》有关仲裁与国家豁免的规定最为全面。13 但从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两部国内立法的实际操作空间十分有限,且有关法院对于“商业活动”的解释较为狭窄且严格,故在实践中往往不能保障ICSID裁决得到实际执行。并且国内立法相较于一般国际法规则的不稳定性更大,主权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国内司法程序修改相关国家主权豁免的立法,从而加大ICSID裁决实际执行的困难。
三、涉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障碍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至今已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造成巨大影响,尤其是在国际投资领域。根据《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中国自2016年起引入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流量以平均每年2.525%的比率增长,引出FDI流量以平均每年2.9%的比率增长。14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为“一带一路”建设所提供的司法服务也渐趋完善。201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加强承认与执行涉“一带一路”仲裁的司法审查,保障仲裁机制能够为加强“一带一路”司法保障、化解投资纠纷发挥积极作用。201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第二批)中,中国认定与新加坡之间的互惠关系,首次承认和执行了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这体现了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提供有力司法服务的决心,也打开了人民法院执行涉“一带一路”生效裁判文书的新局面。此外,2017年9月19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以下简称“贸仲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以下简称《投资仲裁规则》)。《投资仲裁规则》的出台,填补了中国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的空白,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投资仲裁实践,为中国企业提供解决与东道国投资争端的制度化保障,为营造中国更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迈出了坚实一步。15 由此可见,中国司法机关和仲裁机构为提高“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争议解决服务水平不断在做出尝试,其重点是推动国际投资仲裁制度在中国的完善,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仍然是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
在上述“一带一路”建设相关配套司法服务中,我们应当重视涉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相关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不论是ICSID还是非ICSID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其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均存在制度阻碍。
(一)涉华ICSID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可能遭到中国仲裁司法审查制度的阻碍
截至目前,涉华国际投资争议在ICSID仲裁机制项下均止步于管辖权争议阶段,自然也就没有涉华ICSID仲裁裁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实践案例。虽然实践中没有涉华ICSID仲裁裁决在中国法院进入承认与执行程序,但结合《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可以推知将来涉华ICSID仲裁裁决在中国法院进行承认和执行时可能遭遇中国仲裁司法审查制度的障碍。
2017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7〕22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法释〔2017〕21号)(以下合称《最高院仲裁司法审查规定》),两部司法解释都已生效。此次颁布的《最高院仲裁司法审查规定》是继《民事诉讼法》《仲裁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颁布并修订后,再一次以规范性文件形式重述中国《仲裁法》的适用及中国仲裁司法审查制度。《最高院仲裁司法审查规定》最大的亮点是其列明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的六种类型 16,并且人民法院在进行仲裁司法审查时不再区分涉外仲裁机构与非涉外仲裁机构所作出的裁决,统一适用《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17
虽然此次颁布的《最高院仲裁司法审查规定》加强了仲裁司法审查的统一归口管理,并系统完善了仲裁司法审查的实务操作规程,具有支持仲裁发展的积极意义,但它们共同构成的仲裁司法审查制度在实践中可能不符合《华盛顿公约》所确立的ICSID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不适应涉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的要求。具体而言,根据《华盛顿公约》第53条,该公约的缔约国在ICSID仲裁庭发布最终裁决后被禁止采取其他非《华盛顿公约》机制(例如执行地国的国内机制)进行救济。而《最高院仲裁司法审查规定》列明的六种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况尽管被认为主要针对的是普通商事仲裁案件,并且迄今为止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并未见到涉及对ICSID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案例,但至少从条文规定文字上从理论上并没有明确将ICSID仲裁案件排除在外。同时《民事诉讼法》第237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仲裁机构裁决制度中 18,也同样未明确无疑地排除该制度适用于ICSID仲裁案件的可能性。因此,ICSID仲裁裁决是有可能在中国的仲裁司法审查制度下被撤销或不予承认和执行的。这也意味着,中国法院若根据前述《最高院仲裁司法审查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拒绝承认和执行ICSID仲裁裁决,就是采取了《华盛顿公约》以外的机制进行救济,而这是被《华盛顿公约》所禁止的。
(二)涉华非ICSID的国际投资争议仲裁裁决无法通过《纽约公约》在中国获得承认与执行
ICSID作为全球最大的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机构,其仲裁庭作出的仲裁裁决可借由《华盛顿公约》的规定进入裁决后的承认与执行阶段。但其他非ICSID仲裁机构,如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以下简称“PCA”)、国际商会仲裁院(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以下简称“ICC”)、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The Arbitration Institute of 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以下简称“SCC”)等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也受理国际投资仲裁案件。这些非ICSID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所作出的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其承认与执行通常来讲需要靠东道国自觉履行、或根据东道国以及申请承认与执行裁决地的国内相关立法进行申请。虽然《纽约公约》本身并没有排除国际投资仲裁裁决适用的空间,但根据《纽约公约》的相关规定,适用《纽约公约》的裁决开启承认与执行程序仍然需要依靠国内法的规定,因此一国法院如依照《纽约公约》开启对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程序,其结果将难以预见。 19
但根据中国加入《纽约公约》时所作的保留 20,涉华非ICSID的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是无法通过《纽约公约》在中国申请承认与执行的。例如,一个中国投资者与日本政府发生了国际投资争议并将争议提交PCA进行仲裁,那么中国投资者就PCA所作出的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是无法通过《纽约公约》在中国申请承认并执行日本在中国的财产,从而加大了中国投资者的维权成本。
综上所述,《最高院仲裁司法审查规定》一方面有意扩大仲裁司法审查制度的覆盖范围,完善中国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加强了《纽约公约》在中国仲裁司法审查制度中的作用。但从中国现行仲裁司法审查制度以及《纽约公约》目前在中国的适用空间看来,中国现行的仲裁承认与执行机制以及仲裁司法审查制度可能不适应涉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包括ICSID与非ICSID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在中国顺利地获得承认与执行。
四、完善涉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制度的构想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涉华国际投资(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国际投资)获得更大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为了给涉华国际投资提供司法保障,进一步促进涉华国际投资的发展,有必要完善涉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制度。针对ICSID作出的涉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中国应当探索建立与《华盛顿公约》相匹配的承认与执行机制以及国家主权豁免制度;而针对其他非ICSID的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以及通过非国际投资仲裁解决的涉华国际投资争议,中国可以借鉴司法互惠关系探索建立仲裁互惠关系并审慎评估《纽约公约》的适用空间。
(一) 探索建立ICSID仲裁裁决承认执行机制与国家主权豁免制度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针对涉华ICSID仲裁裁决,中国需要有与《华盛顿公约》规定的承认与执行机制相配套的仲裁承认与执行机制,此外还需要有国家主权豁免制度的相关立法。
首先,如前文所述,考虑到中国目前的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制度中的司法审查程序有可能不符合ICSID仲裁审议的案件在中国获得承认与执行的要求。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本文认为中国当前的仲裁司法审查制度在明确不适用于ICSID作出的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大前提下,应当重新评估和完善相关仲裁裁决司法审查制度,并加以立法化、确定化。
其次,考虑到中国目前并没有有关国家主权豁免的立法,本文认为应当将国家主权豁免制度的立法工作提上议程,并审慎考虑中国的国家主权豁免制度是应当继续主张完全豁免还是限制豁免。本文认为针对ICSID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国相关国家主权豁免制度应主张限制豁免。一方面,中国目前所主张的国家主权绝对豁免立场,使中国赴外投资的投资者在海外投资受到投资地东道国的侵害时既无法在中国发起国际投资仲裁,也无法在获得有利裁决后在中国执行外国国家的财产;另一方面,在国家主权绝对豁免的立场下,势必动摇外国投资者来中国进行国际投资的信心。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中国目前采用的国家主权绝对豁免立场无法保护中国赴外国投资的投资者,也无法更多更好地吸引外国投资者来中国进行投资,故国家主权完全豁免制度与中国国际投资的发展不相适应。可喜的是虽然中国目前坚持的是完全国家主权豁免,这在中国立法、司法和外交活动中都有所体现,但是中国早在2005年就参与了《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谈判,近年出台的相关法律文件也不断强调仲裁制度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的作用。 21
(二)借鉴司法互惠关系探索并完善通过非ICSID仲裁方式解决的涉华国际投资争议的承认与执行机制
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发布的《第二批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中的第五个案例,即在高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新加坡高等法院民事判决一案中 22,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认定中国与新加坡的司法互惠关系,首次承认与执行了新加坡法院商事判决,这为推动“一带一路”背景下ISDS机制的承认与执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一方面,针对其他非ICSID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可参考司法互惠关系探索建立仲裁互惠关系也是完善国际投资争议在中国承认与执行制度的构想,并可能推动ISDS机制的进一步发展。但这种尝试需要审慎评估《纽约公约》在其中的适用空间,中国的仲裁机构也应当为这种尝试加强对国际投资仲裁的学习。
另一方面,国际投资争议除通过国际投资仲裁外,还可以通过如协商、调解、东道国国内司法救济等多种途径解决。如上文所述,像新加坡法院作出的商事判决,其本质上属于法院判决,亦可以通过国家间司法互惠关系进行承认和执行。但是中国仅与37个国家签订了民商事领域的司法协助条约,其中有32个国家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23,而截至2020年1月,已有138个国家跟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24。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应当积极与他国在民商事领域签订司法协助条约,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此外,中国已签署了于2019年7月2日达成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 该公约的批准和实施将有利于完善涉华国际投资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机制。25
五、结语
总结全文,《华盛顿公约》“自足”的仲裁裁决承认和执行制度中,仅仲裁裁决承认机制保障了ICSID仲裁裁决的权威性和既判力,但在《华盛顿公约》制度本身和国家主权豁免制度的作用下,其执行机制缺乏执行力导致了ICSID仲裁裁决面临难以执行的困境。
聚焦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中国应当注重预防与解决潜在的涉华国际投资争议,而当涉华国际投资争议得到解决后则更应注重相关结果的最终实现。从目前情况看,涉华国际投资仲裁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机制和制度并不完备,中国无法很好承担《华盛顿公约》规定的国际条约义务。因此,为确保涉华国际投资仲裁可以在中国获得良好的承认与执行,中国首先应当探索建立符合《华盛顿公约》的ICSID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机制并开启国家主权豁免的制度设计,其次可以尝试建立国际投资仲裁互惠关系以保障其他非ICSID的国际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获得承认与执行,并积极与他国(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达成在民商事领域的司法互惠协定,从而完善通过其他非国际投资仲裁方式解决的涉华国际投资争议的承认与执行机制。
注释:
* 黄宗劼,上海对外经贸大学2016级国际法学硕士研究生。本文原载《仲裁与法律》第146期。
2.刘笋:《国际投资仲裁引发的若干危机及应对之策述评》,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
3.《关于解决各国和其它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公约》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缔约国对于它本国的一个国民和另一缔约国根据本公约已同意交付或已交付仲裁的争端,不得给予外交保护或提出国际要求,除非该另一缔约国未能遵守和履行对此项争端所作出的裁决。”第二款规定:“在第一款中,外交保护不应包括纯粹为了促进争端的解决而进行的非正式的外交上的交往。”
4.例如,ICSID仲裁庭裁定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订立的投资合同有效、不构成征收或裁定东道国遵照投资合同继续签发许可证等非金钱义务对于投资者而言可能更为有利。
5.Liberian Eastern Timber Corporation v. Republic of Liberia (ICSID Case No. ARB/83/2). 参见《国际法律资料》(1987年第26卷),第695页;《ICSID Review》1999年第2期。转引自余劲松:《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342页。
6.Lucy Reed, Jan Paulsson, Nigel Blackaby, Guide to ICSID Arbitration (Secon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0, p.188.
7.Anastasiia Filipiuk, “Enforcement of ICSID Arbitration Awards And Sovereign Immunity”, http://www.etd.ceu.hu/2016/filipiuk_anastasiia.pdf, July 20, 2020.
8.有学者将其翻译为“商业行为”“商业目的”“商业活动”或“商业资产”,均意为用于商业的国家资产,为方便表述,本文统一表述为“商业活动”。
9.“AIG Capital Partners, Inc., CJSC Tema Real Estate Company v. Kazakhstan (ICSID Case No. ARB/01/6)”, https://www.italaw.com/sites/default/files/case-documents/italaw3077.pdf, July 20, 2020.
10.“AIG Capital Partners Inc. and Another v. Republic of Kazakhstan (National Bank of Kazakhstan Intervening), Queen’s Bench Division of the High Court of England and Wales, October 20, 2005, [2005] E.W.H.C. Comm. 2239, 129 I.L.R. 589, 589-628 (2007)”, https://www.italaw.com/sites/default/files/case-documents/ita0022.pdf, July 20,2020. R. Doak Bishop, James Crawford, et al., Foreign Investment Disputes: Cases, Materials and Commentary (Secon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4, pp.1264-1271.
11.“AIG Capital Partners Inc. and Another v. Republic of Kazakhstan (National Bank of Kazakhstan Intervening), Queen’s Bench Division of the High Court of England and Wales, October 20, 2005, [2005] E.W.H.C. Comm. 2239, 129 I.L.R. 589, 589-628, para.58 (2007)”, https://www.italaw.com/sites/default/files/case-documents/ita0022.pdf, July 20, 2020.
12.“AIG Capital Partners, Inc., CJSC Tema Real Estate Company v. Kazakhstan (ICSID Case No. ARB/01/6)”, https://www.italaw.com/sites/default/files/case-documents/italaw3077.pdf, July 20, 2020.
13.杨玲:《论条约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以ICSID裁决执行为中心》,载《法学评论》2012年第6期。
14.《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国别报告:中国》(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0-Country Fact Sheet: China),载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网站:https://unctad.org/sections/dite_dir/docs/wir2020/wir20_fs_cn_en.pdf,2020年7月20日最后访问。
15.贸仲委《投资仲裁规则》新闻发布会通讯稿,载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网站,http://www.cietac.org.cn/index.php?m=Article&a=show&id=14450,2020年7月20日最后访问。
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一条作出了相同的规定:“本规定所称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包括下列案件:(一)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件;(二)申请执行我国内地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案件;(三)申请撤销我国内地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案件;(四)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仲裁裁决案件;(五)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件;(六)其他仲裁司法审查案件。”
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仲裁司法审查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非涉外仲裁裁决案件的审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申请执行我国内地仲裁机构作出的涉外仲裁裁决案件的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的规定。”
18.《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对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向仲裁机构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裁定书应当送达双方当事人和仲裁机构。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19.池漫郊:《国际仲裁体制的若干问题及完善》,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17页。
20.根据中国加入该公约时所作的商事保留声明,中国仅对按照我国法律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适用《纽约公约》。所谓“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具体的是指由于合同、侵权或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货物买卖、财产租赁、工程承包、加工承揽、技术转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勘探开发自然资源、保险、信贷、劳务、代理、咨询服务和海上、民用航空、铁路、公路的客货运输以及产品责任、环境污染、海上事故和所有权争议等,但不包括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
21.全小莲、刘步蟾:《“一带一路”司法服务中的ISDS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载《人民法治》2018年第3期。
22.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批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载最高人民法院网站: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4722.html,2019年9月28日最后访问。
23.中国目前在民商事领域仅与37个国家签订了司法协助条约,分别为阿尔及利亚、阿根廷、阿联酋、埃及、埃塞俄比亚、巴西、白俄罗斯、保加利亚、波黑、波兰、朝鲜、俄罗斯、法国、古巴、哈萨克斯坦、韩国、吉尔吉斯斯坦、科威特、老挝、立陶宛、罗马尼亚、蒙古、秘鲁、摩洛哥、塞浦路斯、塔吉克斯坦、泰国、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西班牙、希腊、新加坡、匈牙利、意大利、越南。除阿根廷、巴西、朝鲜、法国与西班牙外均为“一带一路”沿线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网站整理:
http://www.moj.gov.cn/Department/node_358.html,2020年8月6日最后访问。
24.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载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gbjg/gbgk/77073.htm,2020年8月6日最后访问。
25.《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22届外交大会通过<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载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官网:http://cicc.court.gov.cn/html/1/218/149/156/1271.html,2020年8月7日最后访问。

